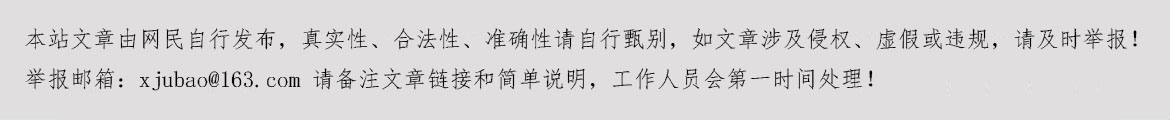高三艺体生文化培训 https://www.dsjptxx.com
文/梅兴无
1936年2月,一位长须飘逸、身着长衫、年近花甲的老人参加了红军,并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就是前清贡生,被誉为“秀才红军”的周素园。毛泽东曾盛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王震:“碰到一个读马列的地主”
1936年2月,红2、6军团长征抵达黔西北地区。2月6日,在行进中击溃敌宋醒保安旅一个营,占领了大定县城。在毕节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派地下党员到大定与红军联系,红军立即向毕节进军。2月9日,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红军歼敌保安团一部,顺利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
红军进城后,按照政策选择富户打土豪,没收地主浮财。一连指导员带人开进了周素园的宅院,没收他家的东西。令指导员惊异的是,周素园对红军并不害怕,说:“我是剥削了农民,但我这个地主跟别的地主不一样,我是拥护红军、拥护革命的。”让指导员更加惊异的是,在周素园的书柜里翻出好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书中密圈细点,说明书的主人仔细地阅读过,而且还有读书的笔记。指导员把这些书和笔记本带了回去,向红6军团政委王震作了汇报。王震也颇感诧异:“碰到一个读马列的地主?”当即决定亲自上门会会这位周老先生。
周素园1879年3月7日出生于贵州毕节的一个书香家庭,16岁中秀才,19岁中贡生。辛亥革命前,他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日报《黔报》,复与张百麟创办了贵州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在武昌首义的影响下,贵州自治学社以新军为主体,于1911年11月3日举行起义,成立了贵州军政府,周素园被推举为行政总理。后唐继尧的滇军入黔,窃取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周素园被迫流亡于京、汉、沪、渝等地,先后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众两院秘书,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秘书。1921年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主政,邀周素园任省政务厅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身亡后,贵州陷入一片混乱。袁祖铭回黔主政,平定贵州乱局,周素园仍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但袁祖铭为一己之私,将贵州再次拖入军阀混战之中。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长征到达毕节。周素园出任由我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后追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图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
周素园痛恨军阀混战,于1925年愤然辞职回到老家毕节,用积蓄“买了2000元的田,典了800元的房子”。他在失意和彷徨中闭门读书,无意间接触到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潜心研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在研究中还初步认识了用马列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和红军。
了解到周素园的这些情况后,王震笑问:“周老先生,你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又是地主,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呀?”周素园坦然道:“我是当过大官,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是地主,但没发过不义之财。何须跑?”王震点点头,又问:“你为什么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啊?”周素园笑了:“中国总得找一条光明之路嘛!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听了他的话,王震兴趣更浓,试探着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赞成,完全赞成。”
王震当即决定退还没收周素园家的东西,后又几次与他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王震跟他开玩笑:“周老先生,您老可不能老是关起门在家里闹革命(即闭门读马列)啊!”周素园确信有一条光明之途就在眼前:“你们来了,我要走出家门闹革命啦!”
贺龙:“抬着他和我们一路走”
王震向贺龙、任弼时报告了周素园的情况,贺、任也非常关注,登门同周素园促膝谈心,介绍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认为他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可信赖的同盟者。
红军在毕节期间,邓止戈联络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反蒋地方武装共约5000人。红军遂将其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任命周素园出任总司令,邓止戈任参谋长,军部就设在周素园府中。贺龙紧紧握住周素园的手说:“欢迎你,‘秀才红军’!”
曾经的国民党高官,年近花甲的富绅地主,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周素园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诚如他在给国民党CC系元老张道藩的信中所言:
这就不能不说是南京的对日政策逼我走上了这条路。“九一八”以来,四五年间主权领土丧失几何?而政府一次退让,三次四次仍是退让。我觉得与其垂老而当亡国奴,不如同情抗敌的队伍,把这根老骨头投掷荒原,或可对麻木懵懂的群众刺激他们一下,使大家赶紧觉悟,一致救国。
周素园的行动,在毕节地区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上层开明人士开始支持红军,使得红军在毕节地区建立农会和扩充红军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周素园积极投入繁忙的贵州抗日救国军事务,还按照贺龙、任弼时等的要求,利用旧的社会关系,给孙渡等滇军高层写信,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他在给孙渡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崧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是你们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此言击中了孙渡的软肋,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滇军,他们在西线按兵不动,使得红2、6军团腾出手来对付东线“进剿”之敌。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后来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二十天,休整补充。”
1936年3月1日,已然57岁的周素园不顾年高体弱,执意与邓止戈率贵州抗日救国军二支队随红2、6军团继续长征。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既要与围追堵截之敌作战,又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周素园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咬牙坚持着。
红2、6军团抵达云南边境倘塘镇,将贵州抗日救国军二支队改编为6军团18师52团。贺龙考虑到周素园年高体弱,经常犯病,还有抽鸦片的嗜好,北上征途更加艰苦,担心他吃不消,决定安排一些黄金、现款,送他去香港暂做“寓公”,并继续为党做些统战工作。王震向周素园转达了贺龙的意见。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快60岁了,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我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闻报,一拍大腿说:“好啊,老先生有骨气!我就欣赏这样的人!我们就是拿18个人抬,也要抬着他和我们一路走!”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给了周素园无微不至的照顾。贺龙曾亲自背着他过河。他随红6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王震“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王震语)。一路上,他患病时战士们用滑竿抬着他行军;身体稍有好转,就执意骑马行军。他竟然不用别人搀扶,翻越了格罗湾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1936年7月初,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7月5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周素园看到了李宗仁等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时的通电,即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名义在红军电台发表了《对李宗仁元电广播稿》,支持“两广事变”,呼吁李宗仁能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
考虑到周素园年迈体弱,让他随红军总政治部一起行动。他这样描述一路的艰辛:“那几个月,睡的是露天下的绿草。虽说有个布篷,但遇到大雨就困在草荡里。而且两三间铺宽的地方,要到30来个人,真是手足都没处安放。只要你抽身一动,就休想再能插下去。吃的呢,简直和猪食差不多……满身是虱子,随便捕捉就是几十上百。”
10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州,成立了甘肃省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周素园被任命为教育部长。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12月2日,周素园随红军大部队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
在长征中,周素园体验到另一种感动:“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驻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他还写信告诉家人:“你或者怀疑说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我不唯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意外,连我自己也预想不到。”
毛泽东:“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
在保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会见了周素园。毛泽东多次同他长谈,鼓励他继续学习与工作,并安排他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陕北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周素园却受到了特殊优待,每月给他10元零花钱,每天从馆子给他叫菜,住在交际处招待所。
在红军大学,周素园有机会广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心情非常愉悦,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刻的我和从前的我完全两样,对于种种关系,都看得极空阔,极潇洒,把旧日那些迂谨固执的性格都冰消云散了。”为了教学需要,他为红军大学编写近代史教材《洪宪叛国始末记》,讲述了袁世凯的发迹和复辟帝制失败的经过。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他为《红色中华》写了《纪念一二八的感想》一稿。应美国纽约《新历史社》之约,撰写了《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一文,提出只有实现人类权力平等,放弃人压迫人的制度,只有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放弃人剥削人的制度,才是消灭战争的基本方法。
西安事变发生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素园以桑梓之情分别给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国民党军政部长兼代总司何应钦,与蒋介石“私交可谓綦笃”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以及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家乡人王伯群等写信,称“伏望跃马横刀,毅然决然当与倭人绝缘,担任艰巨。”“先生为国家危亡起见,为民族生存起见,即犯颜割席,予蒋先生以剧烈的激刺,而发其猛省,事未尝不可为。”希望“顺应舆情,一致抗日”。周素园的信,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37年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停顿时,周素园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给冯玉祥、吴忠信、张道藩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早日实现。
抗战全面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在准备随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前,修家书一封:
余本不欲写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事后如有随军移动情事,再为函告。否则最多只打算每月写一次信,聊报平安而已!人人都知道国事危急,人人都觉得不干我事,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有些人甚至开讲演、写文章,说得义愤填膺,责无旁贷的,枪声还没有响,早就藏到安全地带去了。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国难则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他在后来的家信中称,这封信是作为遗嘱来写的。可见为了抗日,他已做了牺牲的准备。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周素园的回信。
正当周素园准备“执戈以从赴国难”之际,他的身体却未遂其愿。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双脚红肿,流血流水,生活不能自理。贺龙、萧克十分关心,让其夫人蹇先任、蹇先佛常去看他,帮他缝补浆洗。周素园很是内疚,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回信: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十月六日
临行前,毛泽东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地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送上自传,毛泽东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别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做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邓小平:“只要有你名字摆在那里就好”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离开延安,经西安、汉口抵达重庆,边治病边凭借过去在政界、军界的威望,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要求释放政治犯,驳斥国民党内顽固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经他多方努力,国民党四川代理省主席邓汉祥答应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允诺将彭德怀《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各界阅读。周素园把成都活动情况写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是欣慰。
1938年初,周素园受龙云之邀来到昆明,逗留了80天,受到一些开明上层人士的礼遇,周素园趁机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同群众广泛接触,把延安寄来的书籍分发给进步青年阅读,还介绍朱家壁等一批热血青年去了延安。在他的鼓励下,民族资本家郑一斋慷慨捐助购买2万盒治疗创伤的特效药“白仙丹”(云南白药),邮寄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前线救治伤员。周素园的进步活动惹恼了国民党顽固派,限令他离开昆明。
4月,周素园回到贵阳。贵州反动当局早已得到成、昆两地特务机关的密报,对他进行防范和监视,他在贵阳也呆不下去,只好回毕节。周素园向亲友们讲述他亲身参加长征的经过,讲述毛泽东、贺龙等对他的关心照顾,言辞中表达了对他们的钦佩和想念。
延安方面也没有忘记周素园。重庆的《新华日报》长期对他赠阅。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初,请贵州著名教育家、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从延安带了一条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毛毯赠送周素园。由于种种原因,毛毯未曾收到。解放后周素园到北京开会,中央统战部金城对他说起此事,他心情十分激动。周素园在195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可见毛主席在极忙碌极艰苦时,还记得有我这一个人。”
1949年11月,解放军挺进贵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周素园不顾年迈多病,组织毕节支前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为解放军准备粮秣,维持地方秩序。11月27日,他和群众一起迎来了毕节的解放。这一天,他把自己的《待尽日记》更名为《光明日记》,并在扉页上写下:“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他给毛泽东发电:“北京毛主席,别来十二年,衰朽余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周素园叩艳(29日)。”
接着,周素园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开展肃清残敌和土匪的斗争,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恢复秩序。他写信给国民党军师长刘鹤鸣等,争取到他们起义。在他的劝说下,毕节专员廖兴序、毕节县长吴庭芳相继投诚。
◆周素园(右)与贵州省政府主席杨勇(中)合影。
1950年2月,周素园应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之邀请,来到贵阳。他不顾年过古稀、体弱多病,在贵阳广泛地接触社会各方面的上层代表人物,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思想、意见和要求反映给省委领导,对贵州解放初期的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7月下旬,周素园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身份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大会,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领导人。他与阔别12年的贺龙叙旧,贺龙风趣地说:“你是死不得的。我们都希望你再活20年,享受享受,以清偿长征的辛苦。”贺龙及刘伯承、邓小平提议周素园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素园先以年老病弱婉辞。刘伯承说:“素老年高,我们会缜密考虑的,平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邓小平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有你名字摆在那里就好。”这样,周素园担任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当选为贵州省副省长。
1951年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全委会。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交谈40分钟。周素园提出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希望能早日大规模开发。毛泽东说,没有铁路,你们那矿能运得出来吗?周素园提出自己年老体弱,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有困难。毛泽东说,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是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什么都好了。以后政协开会,你能来就来,不能来不要勉强,总之,以身体为第一。第二天,周素园又给毛泽东写信,并呈交了《开发及扩充贵州矿业建设》等建议。
周素园平生酷爱读书,从1950年到1958年,他研读过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30余种,每有心得体会,就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他一生留下著述300多万字,主要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军史述要》等,其中具有代表性著述收入《周素园文集》公开出版,王震为该书作序。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去世,享年80岁。贺龙于2月2日发唁电:“惊悉周素园副省长逝世,殊感哀悼,特电吊唁。”王震在《周素园文集·序》中称:“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侵权必究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